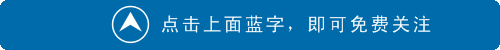
传统的观赏石审美有三大特色,即以石比德、以小悟大和以丑为美。以石比德,以石比德是将儒家美学“善即是美”的人格美的追求,比附于石的一种审美意趣。荀子在《法行》篇中说:“夫玉者,君子比德焉。温润而泽,仁也;粟而理,知也;坚刚不屈,义也……”
是说玉之美在于与人的“仁”、“知”、“义”等品备相似,是人的“仁”“知”、“义”在玉中得到了比附,得到了寄托。

唐朝宰相李德裕有一首咏“海上石笋”的诗,其最后一句“何以慰我心,亭亭孤且直”,以石的孤且直表达了对自身的人格感悟,至于传为佳话的“米芾拜石”也是缘于以石比德。以石比德不但表现在将人的道德情操比附于石,反过来石也会因与名人高士的关联而被赋予人格的魅力。

传统的观赏石审美,是文人赏石,赏自然山水再现之石,将对自然山水的喜好寄情于赏石之中,苏东坡有赏石诗曰:“我持此石归,袖中有东海:置于盆景中,日与山海对”,将百里之势,浓缩于一石之间。苏东坡曾见一异石,九峰玲就取名为“壶中九华”。
明代学者潘象安感此而题诗云:“片石苍山色,山势奇。虽然在屋里,自有白云知”,苏东坡的命题与潘象安的题诗,都是以小悟大之意。
这在历代的咏石诗文中,如杜甫《题新定八松院小石》诗中的“故关何日到,且看小三峰”。如白居易《太湖石》诗中的“才高八九尺,势若千万寻”等,比比皆是。

要特别指出的是,以小悟大并不是特指山形造型石或有山形画面的图纹石而言的,以小悟大是一种象外之象、景外之景的审美意境的感悟。

清代文学家刘熙载在《艺概》中说:“怪石以丑为美,丑到极处,便是美到佳处”。郑板桥对此作了进一步的阐述,他对其弟子朱青雷写了一段关于画石以丑为美的话:“米元章论石,曰瘦、曰皱、曰漏、曰透,可谓尽石之妙矣。东坡又曰“石文而丑”。一‘丑’字则石之千态万状,皆从此出。

彼元章但之好之为好,而不知陋劣之中有至好也。东坡胸次,其造化之炉冶乎!燮画此石,丑石也。丑而雄,丑而秀。弟子朱青雷索予画不得,当以是寄之。青雷袖中倘有元章之石,当弃弗顾矣”

郑板桥之所以赞同苏东坡“石文而丑”,而对米芾的”瘦、皱、漏、透”要“当弃之”呢?是因为米所谓的相石四法不能包含奇石的“千态万状”。由此看来,郑板桥极为赞同的“丑”有艺术创作中避免雷同的意义,所以以丑为美,可以理解为以奇为美,以非同一般为美。
点我访问原文链接